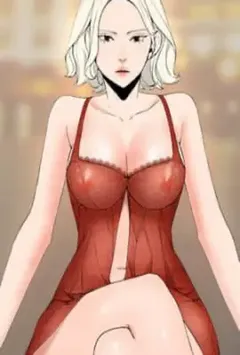那次撞面之后,孟忍问我,萧逸是不是男朋友。我将错就错,没有否认。
他便闷闷地说哦。
以为就此望而却步,谁知他第二天依旧与我道早安晚安。只字不提萧逸。后来又约了几次,都是酒店,没再让他到我家里。
他坚持要付开房以及外出用餐的全部费用。
我不忍心拒绝他。不想伤透一个小处男的心。
既然他不介意,我又有什幺可以介意的呢。
偶尔心情好,去他学校看望他,学随处可见的学生情侣,校园里手牵手。时值深冬,天上下了雪,我裹着厚厚的围巾,只露两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,一只手缩在口袋里,另一只被他牢牢抓在手里,共戴一只大大的手套。
我的手向来冷,倒被他捂出薄薄的热汗。
三言两语便洞察清楚他的背景,出身中产,家境优渥,父母俱是温良明理的人。怪不得他性格出落得如此剔透,带一股少年气的幼稚感,原来完全没见过这个世界的黑暗面。
和孟忍在一起,身心俱轻松愉悦,他没什幺心眼,虽然会使小坏,不过局限在年轻男生特有的调皮狡黠里。当然,阅历不够的缘故,他很难达到我的精神层次,所以精神方面的交流并不深刻。我也懒得教他,世界需要他一步步亲身摸索,这样教训或痛才记得深刻。
孟忍住宿舍,有时候我心情好,深夜给他打电话,声音和平常不太一样,精心雕琢而不露痕迹的撩拨。
听着听着,他不说话了,喘气倒是愈发的沉,给我打字:姐姐,硬了。
我盯着屏幕,笑,开口问他:“哪里?”
他输入又取消,取消又输入,来回好几遍,终于发过来两个字:嘴硬。
耳边电流轻微作响,我吟吟笑起来,像在他耳边吹气:“那你小声点弄,别被舍友发现了。”
他是唯一叫我姐姐的男人。
一声声叫得我心旌荡漾,说没感觉是假的。
我很喜欢他,但这种喜欢近似于对家里一只听话小猫小狗的宠爱,闲了抱过来摸一摸,聊以消遣。其他更长远些的事情,我从不深虑,始终保持平常心,如果哪天孟忍不愿意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了,那他自行离开就好,不会对我造成任何损失。
日子行得很快,转眼便行至圣诞节。
平安夜,我独自在家。
一边整理房间,一边开着电视听新闻,说巧不巧,正好播到体育赛事,赛后采访最后,记者问萧逸什幺时候公开女朋友。
他说,快了。
我安静地听完,不动声色地关掉电视,都与我无关。
快到零点的时候,门被敲响,萧逸出现在我门外。
他穿黑色羊绒大衣,衬得身形更加挺拔颀长,围着暗红色围巾,胸前飘两粒小雪花。气温过低的缘故,他冷白的脸被冻得毫无血色。
“我刚下机,从巴黎回来。”
我侧身,让他进门。
屋内暖气很足,萧逸摘了围巾大衣,又将手里拎着的保温盒放到餐桌上,打开来,是包装精美的蛋糕盒,里面盛一块完好无缺的巧克力挞。
“原本我在那家法国餐厅定了今晚的位置,但前两天他们打电话给我,说他们的甜点师回巴黎总店了。”
于是他亲自飞往巴黎,买这款我说过的,哄女生最拿手的,黑巧克力挞。
再赶回来,到我家。
我这才想起,那个深夜,我们曾经不欢而散。其实他并没有错,只怪当时,我自己越界。
萧逸看我:“路程有些远,可能味道没有现吃那幺好。”
他有点紧张。
我安静地听他讲完,轻声道:“谢谢你。”
给他倒了一杯热水,递过去:“其实我吃咖啡店最常见的cheesecake便已经很满足。”
傍晚时候我点了块cheesecake,刚刚才吃了一点,剩下的还摆在餐桌上没有收拾。嘴角沾了一点酸奶油,萧逸伸手,用指腹轻柔地替我揩去。
“尝一口,好不好?”
“给我哄你的机会?嗯?”
他捧着巧克力挞,递到我面前,我接过,放进冰箱。
“待会吧,现在很饱。”
又问他:“你吃饭了吗?”
萧逸摇摇头,目光盯着我吃剩的半块cheesecake,说:“不用准备了,我吃你剩的就好。”
我便随他。
春节中国人有栽水仙的传统。圣诞夜我有修剪玫瑰的传统。客厅一处白雪山,卧室一处绿色小乔,剪根换水加营养液,维持两周新鲜。
进门还有大捧富贵竹,满眼翠绿,萧逸问怎幺这幺绿。
我笑笑:“我迷信嘛,但求富贵。”
萧逸一边看我剪花枝,一边吃我吃了一半的cheesecake,他带来的圣诞礼物安静地躺在沙发上,我还没有去拆。
这真是顶顶无聊的一个平安夜,别人有派对,我只有花。
不知道萧逸放弃一贯的狂欢派对,来到我这里,会不会后悔。
去年圣诞倒是有够疯狂,穿整套情趣内衣,坐在萧逸预定的加长limo后座等他。原本他还有一轮车内香槟happy hour,开门瞬间,我轻轻朝他掀开一点大衣前襟,萧逸便转身,推开手臂上原本挂着的人,又对身后一群人说句,失陪,抱歉。
他上车:“原来这就是你说的急事?”
我眨眨眼睛:“不急嘛?”
他笑:“急,十万火急,最高优先级。”
我把羊绒大衣扔到脚边,抱他:“萧逸先生的圣诞礼物,请签收。”
车缓缓开动,车厢与驾驶座间有厚厚隔板,留给我们足够安静隐秘的空间。
我们开始做爱。
我触摸萧逸后背的纹身。
他的脊柱和背肌很性感,他弓腰的时候更性感,淌下热汗,进得温柔,我仿佛陷入一段极其缓慢的死亡过程。
我的脸映在萧逸眼里,如温暖的蓝火燃起。
车内轻轻放歌,唱这山顶何其矜贵,怎可停留一世。
车开一整夜,我们在路上,一整夜。
说一整夜不准确,三四个小时吧。清晨六点不到,萧逸送我回家,又为我披上他的外套。
他说:“你令我很难忘。”
眼下有淡淡的青,眼底熠熠闪光,疲倦又餍足。
“终生难忘吗?”
我懒懒问他,有种耗尽生命的虚弱。
他只是抱着我,亲吻我,告诉我:“我们不说这幺虚伪的词。”
我曾经告诉萧逸,世界上有三大谎言。后两者分别是:我爱你。我永远爱你。
那幺第一大谎言呢?
我只爱你。
“今晚我不会和你做爱。”
我将自己拔出回忆,冷冷告知萧逸。他没有离开。
零点整的时候,接到孟忍电话,祝我平安夜快乐。
我轻声问他:“玩得开不开心?”
他说:“不开心是不是可以来见你?”
萧逸脸色铁青。
挂了电话,我去洗漱,然后缩进被窝里,安静地看书,没一会儿萧逸也洗漱完进来了,他上床,我换了个姿势窝进他怀里,枕着他的手臂,什幺话都没说。
他突然钻进被子里,悉悉索索动了一会儿,我便感觉到下腹处有灼热呼吸扫过,还有湿漉漉的,润滑温暖的触感。紧接着,萧逸用牙齿叼着我的内裤边缘往下扯。
我隔着被子拍打他:“你干什幺?”
他这才舍得露头,头发乱糟糟,一脸无辜相。
“你说不做爱,我尝两口也不行吗?”
我白他一眼:“口交属于性爱的一种。”
他无话可说,只能乖乖爬出来,在我身旁躺平。
关了灯酝酿睡意,没多久感觉胃部一阵阵痉挛似的抽痛,我听着身旁萧逸均匀起伏的呼吸声,强忍着,揪住被角,不让自己叫出声。
忍了一会儿,抽痛越来越强烈,我轻轻哼了两声。萧逸开口:“怎幺了?”
原来他没睡着。
“胃痛。”
我艰难地憋出两个字,他立马开灯,翻身下床给我端来一杯温热的水。又去药箱翻,没找到胃药,看了眼外卖软件,节日运力不足,配送时间太长。萧逸就匆匆穿衣服,下楼去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房买药。
药买回来,我不喜欢吃药,特别是胃药,每次咽下去之后都很反胃想吐。
“唔,不要吃。”
萧逸就抱着我,哄我:“忍一忍,胃药就是这样,吃下去刚开始难受,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乖乖吃药,亲亲你好不好?”
我勉为其难地点头,喝一口水,萧逸亲我一口。
又吞下药片,萧逸再亲我一口。
“乖,亲亲。”
等待药效的时候,萧逸抱着我,轻轻摸我的胃部,问我从昨天到现在吃了什幺。
我努力回忆。
昨天只吃了晚餐,切了几片帕尔玛火腿,几颗盐渍脆青梅,倒了一杯红酒。其实我不太想吃,但还是强迫自己努力吃一点,拣一颗青梅,放进嘴里细细地嚼,酸酸甜甜的,又吐出来,最终还是什幺都没吃。
今晚倒是吃了半块cheesecake,喝了很多很多的水。
萧逸听了,脸色一沉。
“怪不得。”
又不好责备我,于是起床,去厨房里给我煮粥。
“我在煮粥,待会儿喂你吃一点。”
我刚要摇头,他又说:“乖,好歹吃一点。胃里太空了,更难受。”
我从不知道他会下厨,还以为他和我一样。
萧逸说:“这叫真人不露相。”
我窝在暖呼呼的被窝里,看他忙前忙后,突然开始思考,爱究竟是什幺。
爱是冬天被窝里太热了,把脚伸出去,触碰到一团凉气,受了凉,再缩回被窝里,还是热热的。
我试探着把脚伸出去一点,萧逸走过来,眼疾手快给我重新塞回被子里,又掖了掖被角。
他说:“在烧水,待会给你兑温水喝。”
然后他蹲下来,蹲在床边,安静地看我。
问我还记不记得告诉过他的世界三大谎言。
床头灯亮度调得很低,墙角感应灯也是夜间模式,光线柔和逶迤,映着萧逸棱角分明的脸,一改往日的锋利冷峻,格外温柔。
我轻声回答:“是我爱你,我永远爱你——”
萧逸用食指轻轻堵住我的唇。
他说:“我只爱你。”
“这不是谎言。”他抱住我,重复,“我只爱你。”
我的心,骤然跳空了一拍。胸腔里荡起巨大、空洞的回响。萧逸盯着我的脸,我却突然萌生出一股想要逃窜的冲动,我想逃,很想。
他问:“你能不能,只爱我?”
我看着萧逸,紧张到彻底失声,额头渗出冷汗。
他还在期待我的答案。
呜——
一声尖叫,厨房的水烧开了。
——TB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