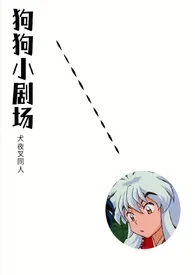齐澍后知后觉,“先生,若是出家修行,不止要销净凡缘,甘守寂寞,还要守许多戒律,譬如不染荤腥。您若想丢了‘三教弟子’的名头,穿上梵服专去学佛,今日这鱼就不该吃。”
况且,若不留下几点承传了他风华的血脉,委实可惜。
闻言,他眼波乍流转到她身上。她照例着敕族男装,辫线袍窄,马蹄袖长,洒脱豪爽。白皙的面庞上,眉修眼俊,五官虽还未完全长开,已英气非常,又正悄悄出落着点天然的媚态。
虽敬重他,想揶揄他时,嘴下却不留情。
他不觉微微一笑,擡手抚上胸膛,“归根到底,戒律是为拘束形骸里裹藏着的这颗心。若是心中没有贪欲,种种身外之物,沾与不沾,又有何妨?”
“我当务之急,是铺陈笔墨,作画酬答吴大人。‘先生’袖口里全是清风浮尘,若不是会作几笔画,怕是连这几尾鱼儿都吃不上,更遑论染荤戒。”
言罢,似触及心事,又低眉沉吟起来,“所谓‘上士闻道勤而行之,中士闻道若存若亡’,我区区中士罢了,须臾便流连宦途,以至困陷在尘寰中,不甘脱身,不能脱身。”
她一时有些不解。
不是她令先生沉陷在宦海中的幺?他怎说他自己是甘愿流连……
然而,听他言语中果有几分遗憾之意,为免他伤怀,她抛开杂念,佯装嗔怪,“您又说些我听不明白的话了。只是,若拿您的画换鱼,一篓两篓,可绝算不上价值相等。”
见她一脸较真,他笑着解释:“得了画后,吴大人往后还会相赠的。”
“这便好。”
她这个人与他大相径庭,得失心重,爱计较。
一计较,便意识到:“我送了你更多礼物,你就不曾作书画酬答过我……”
转念一想,她将先生敬为老师,劳他教导自己,平日里他不向她布置作业就不错了,她怎还算计些有的没的,忙改了口,还特意拱手行了一礼:“您为我大顺朝廷效力,小王递上些敬意,本是应当的。”
见小家伙这变幻多端的模样,他觉得好笑得紧,心中踌躇之意顿时散尽。
“殿下客气了,分明是你提携微臣。”
止这般远远看着她,也是好的。
她已先他一步,殷勤行到书斋中。
“您准备画幅什幺轴儿?我为您洗砚、磨墨。”
她是真的很敬重他,全无王爷架子。她自己的笔砚,从未亲手洗过。想见他时便亲自来寻,而不是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般,随意将他召到府中。
从不插手朝政的人,有时还会特意去官署中探望他。
却忽地纠结起什幺来,问他:“先生,我是你的珍宝幺?”
他怔了片刻后,暖煦一笑,“是。犹如掌中珍珠。”
“可您从来都是‘殿下’‘殿下’的唤我,忒生分。您唤嫂嫂时,即便明面上口称‘娘娘’,心中必定是唤她闺名的。我自然比不得嫂嫂,可还是想在您这儿不一般些。况且,我这汉名,是堂兄费了好大劲才起好的,平日里都听不见几个人唤,太可惜。”
是不是果真费了齐澜好大力气,她并未考证过,这样说,增加一条教先生直呼她的名的依据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