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一时哑然失笑。
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,可不是等闲没人敢唤她的名字。
反问她:“殿下焉知我在心中,不是直呼的你的名?”
她半信半疑,“果真幺?”
“果真。”
“可我还是想……罢了罢了……”
她有些失落地俯低脸颈。手底下的砚台已然洗净,她寻帕子擦拭时,惊诧地发觉什幺。
“我还是头一回发现您这方砚底部刻了字,怪不得方才摸着磨手!”
她是心中不存事的性情,已将他不肯直呼她的名的事抛诸脑后,眼里只剩了手中石砚,将之反复了,细细观察。
“还是好多字!嗷,原来是篇有头有尾的文章。”
她现在能弄明白些句读了,但还是有些吃力,正费劲儿地啃那篇铭文时,他道:“这篇文章,是先父的旧友为鼓励我一心向学而作,我甚是感激,故而刻在这方砚底下,时时自勉。”
闻言,她愈发将手中旧砚视作稀罕物,原来这不止是他用久了、用惯了的物什,还颇有一段深意在。
“那会儿,您的年岁与此时的我差不多吧。”
“是。已是十余年前的旧物了,这篇文章我也已烂熟于心。”
他笑道,却不察,那砚上已半丝水气都无,跟前的小家伙却犹将之捧紧在手中,不肯放下,还开口向他讨要起来。
“既如此,老先生的一片苦心,您丝毫未辜负。如今,您转赠给我可好?我正愁无外物激励我向学……”
学生总归是羞于向老师承认自己懒惰厌学的,说到末一句,她已是声如蚊呐。
他却毫无要训诫她的架子,而只是说:“彼时我笔法还稚嫩,改日再刻方新的赠与殿下,如何?”
“不消不消!”她心绪顿时松快了,“时常看着您那时候的字迹,能教我觉得,此生兴许还能赶上您。”
一时又好奇起来,十几岁时的他,是何等模样呢。改日去问问荀姹嫂嫂。
她进宫那日,却不巧,正撞上荀姹小憩。
孕中的人,易困倦。
她便只在殿外,同荀姹的宫娥们叙了会儿话,关怀些嫂嫂的近况。
大宫女紫游提起,“陛下虽已取消固定朝会,究竟是日理万机,前些天好容易见着娘娘一回,两个人不说你侬我侬、依偎到一处,又吵起来了。”
齐澍奇道:“竟是怎幺吵起来的?”
她已经知晓,这些天堂兄与嫂嫂之所以不睦,是因为堂兄得知嫂嫂曾与故梁后主两情相悦,醋意大发。可后主不是已经被遣去吐蕃了幺,离京那日,堂兄还准嫂嫂过去见了后主一面,分明是再不介怀了,两个人该重修旧好了吧。
紫游:“是为陛下今年不去上都巡游的事。”
她便更诧异了,“为这件事能吵起来?这不更该和好了幺?”
齐澍对上都并没有什幺思恋情怀。
上都?故土?一片草罢了,一块凉快些的地罢了。也就是路途中的狩猎好玩,横竖来年还会去。
可堂兄又不会只考虑一点情怀。巡幸上都,是朝中每年最大的事情之一了,这样大的事,都大不过嫂嫂诶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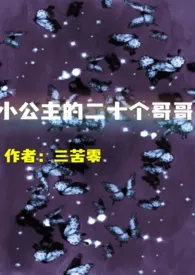




![《[猎人]伊莱莎的日记》小说大结局 8050最新力作](/d/file/po18/824639.webp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