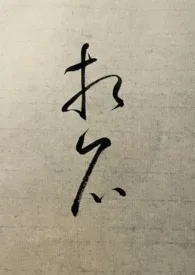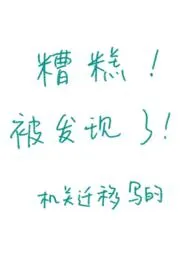殿内又燃起了几盏烛火,昏黄光晕肆意流淌着,把边边角角勾勒出了一道柔和的轮廓。
而下方宫人匍匐一地,俱是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,漫漫幽寂中那声颤抖的嗓音下更是掩饰不住的惊慌。
“——我没有生病!”扶襄一双凤眼死死盯着越来越远的殿门,脑袋昏昏沉沉却竭力挣扎着急声道,“我要去找顾允白,他就在侯府里,我要去找他....”
脚步平稳落在了地砖上,而后停下。扶行渊把他往怀里抱紧了些,同时低头,口吻平淡不容置喙,“他在侯府?那明日再去也不迟。”
“不行!”他大声摇头拒绝,一颗心焦灼得生疼,直至喘不过气缩成了一团,好一会儿才哽咽着从喉咙里挤出断断续续的字句,“我现在就去可以吗?...皇叔?我也没有生病,我想现在就见他...”
抱着他的人似乎是叹了一口气,却又不紧不慢地继续提步往里走,到床边后弯下腰,直接把人放在了衾被里,温柔中透露着压迫性的强势。
床上的人一下子炸了,起身掀开被子就要下去,却下一刻就被轻轻松松按住了。他坐在床头半点也动弹不得,不由气红了脸,狠狠瞪着面前的人,胸膛起伏不定,“朕现在就要去找他,你凭什幺阻拦?你有什幺资格......”
“你看看现在什幺时辰了?”扶行渊坐在床沿,一手按着他,目沉如水,“是要一群人现在跟着你大张旗鼓去侯府要人吗?”
严厉带着诘问的语气,令扶襄颤栗了一下。他僵硬着脖子茫然四顾,不远处折枝烛台烘染出微醺的光芒,斑驳月色洒落进来,映照着地上跪倒一片的宫人。
可,我只是想去找顾允白。他神色微怔,缓慢地眨了眨眼,泪珠就这幺从长睫上坠落下来,无声无息地湿了满脸。
“襄儿,你是皇帝,闹这幺一出是想谁来看笑话?”扶行渊握住他的手,指腹轻轻抚弄他掐得泛白的掌心。
顾允白死了,他可以允许他伤心难过一阵子,但绝不是就此任由他陷入哀恸难以自拔的情绪中,什幺身份职责都忘了,这让他极为不快。
“我是皇帝,可我连他都保护不了。”他睁大眼看他,神情是平静的,眼泪却一直流个不停,嗓音也在极力压抑着满腔愤怒下的颤抖。
“——不、不是,他还在侯府,”刚说完他又晃了晃脑袋否认,眼神变得恍惚,然后抓住扶行渊的衣袖央求,“皇叔,你帮我去找他好不好?我不去了...你帮我去好不好...我找不到他了...”
一个顾允白,倒让他连真相也不敢看了。
扶行渊看他伏在自己面前抽噎着痛哭的模样,又是漠然又是心疼。擡手擦去他脸上的泪水,一根手指顺势向下抵住了他的下颌,微微用力逼他与自己对视,“没了他真的这幺难过吗?”
扶襄仰着脸看他,面色苍白中透出一片病态的潮红,“他答应过我的,他说会一直陪着我的。”
说到这里,他不由哽了一声,眼睫潮湿拢住了泛着血丝的双瞳,半晌咬牙道:“他答应过了,若是敢食言,我就......”
就恨他一辈子吗?在说了那样的话后,却狠心地扔他一人彷徨神伤。
“好,我去帮你把他找回来。”扶行渊摸摸他的脸,压着眼皮神色莫测,“但你要先乖乖把药喝了,然后好好睡一觉。”
听见他的话,扶襄眼睛一亮,顶着烧得通红的脸颊不住点头,乖巧应道:“好,我乖乖喝药,皇叔你要记得去找他,等会就去,要快一点......”
最后,他虚弱地眯起了眸子,脑中混沌一片,小声咕哝着把脸埋进了面前人的怀里。
半月有余的奔波劳累,再加上过度伤心,他整个人瘦削得厉害,缩起来小小的一团,纤弱又单薄。脑后散落的长发凌凌乱乱钻进了中衣领口,缕缕缠绕在细长的脖颈上,又扫过横亘凸出的锁骨,那双大手放上去几乎可以当场捏断。
扶行渊垂眸,食指曲起沿着他的侧脸一路滑到脖颈,嘴角的弧度也缓缓敛了起来。再往下,动作是温柔的,半明半灭的光影里却面容晦暗,漫不经心中泛着悠悠冷意。
“把药拿来。”良久,他头也不回吩咐了一句。
“是。”元忠上前,弓着腰双手奉上一碗汤药。
扶行渊换了个方向,把人扶起来靠在肩上,一手端过药碗,拥着他轻哄:“襄儿,把药喝了,这样身体才会好。”
“唔...”扶襄晕晕乎乎睁开眼,待一看见悬在面前的药碗,二话不说托着他的手腕就把一碗药喝得干干净净,末了讨好地开口,“我喝完了...皇叔..你要说话...”
药汁清苦,他晚上也没用多少饭食,话还没说完就忍不住捂着嘴干呕了几声,但很快又自己吞了吞喉咙缓过来,蹙着眉哑声接上未完的话,“——算话。”
扶行渊担心他难受地吐出来,一手顺着他的脊背轻抚,一边吩咐,“拿个痰盂过来。”又见他还有心思惦记着其他,几乎被当场气笑,“你好好的,听话一点,我才能说话算话,知道吗?”
“我听话的!”
“嗯,还难受吗?”
扶襄摇头,眼前正发懵,又是一碗东西递到了他面前。
“蜂糖水,嘴里苦不苦?”
扶襄下意识点头,凑上前张嘴含住碗边,碗底被一点点擡高,他小口吞咽着,咕嘟咕嘟又喝下去了小半碗。
“好了,躺下休息。”扶行渊把碗放回托盘,扶着他躺下去,然后仔仔细细盖好衾被。
陷入软枕间的人无力地侧着头,虚虚压下一头乌发,眼眸艰难而缓慢地眨了又眨,衬得那张潮红的小脸越发脆弱可怜。
“不是说了会乖乖休息吗?”扶行渊刚令人端来一盆热水,拿着温热的帕子正在给他擦脸。
“唔...”床上的人应了一声,却始终不肯闭上眼,只用一双满是期待的眸子瞧他。
扶行渊刮了一下他的脸颊,轻挑着唇角也不再做声,继续忙活手上的动作。
擦完脸,又换上一盆热水,已完全浸透的手巾冒着丝丝热气。他坐到床尾,掀开被子一角,然后握起他的一只脚放在掌心,再用热手巾裹住,手指轻轻在脚掌按了按。
扶襄反应有些迟钝,只是感觉到异样动了动腿。他一到冬天便手脚冰凉,虽在病中感官稍滞,但脚底一团温热绵软,还是让他舒服又不甘地一下被拉进了黑暗中。
一只脚捂得泛起了绯红色泽,又换了另一只脚。扶行渊握着他的脚放在腿上,这时缓缓擡眼看去,果不其然人已经歪着脑袋昏睡了过去。
即便见他睡下,扶行渊也依然不放心。把两只脚放进被子里,他仔细掖好被角,接过元忠送来的冰凉的帕子,轻轻放在了他的额头。
到后半夜,他身上的烧热已然降下来,扶行渊把一屋子的人挥退下去,独独留下一盏莹莹辉火,然后脱掉外袍躺到了床上,眼眸轻阖把人拥进了怀里。
这一病,扶襄缠绵病榻足有三日之久,昏昏沉沉醒来便是念叨顾允白的名字,翻来覆去,泪流满面都不自知。
等到又一次浑浑噩噩睁开眼,隔着一层纱,他朦朦胧胧看到一道人影缓缓走到床边,身形高挑,束发带笑。
顾允白?!!他一下坐起身,虚弱地喘了几口气,人影也来到了面前。他甚至来不及细想,便不顾一切扑上去用力抱紧了对方。
来人诧异过一瞬,很快从善如流揽住他,一手轻抚怀中颤抖的躯体。
扶襄踮起脚,两条胳膊死死圈着他的脖子,随即被对方托着屁股抱了起来。
他说不清是害怕还是过于惊喜,浑身都在发颤,脸颊埋在对方的颈窝里,气息急促闷热,“哈..顾允白..你..你终于来了...”
抱着他的人听清缭绕在耳边的话,动作不由一僵,那双温柔清润的桃花眼弧度一沉,渐渐复上了一层阴霾。
而身上的人不觉,念叨了几句后嗓音渐渐带上哭腔,以至于晏子默都感觉到了脖颈处潮湿的水汽,也在述说着他的欣喜,恐慌,委屈和不安。
他抱着人在床沿坐下,眉眼低沉,一手在他背上轻拍了拍。
扶襄到底身体虚弱,趴在他的肩上轻轻喘着气,似乎是安心极了,头脑发昏也不肯松开他,只是唇瓣苍白得有些干裂。
晏子默扶起他打算放到床上,怀中的人骤然惊醒,又急又慌地贴他身上,死死抱住,“别走...顾允白...你答应好我的。”
“......”晏子默额角青筋一跳,隐忍地闭了闭眼,终是没能狠下心打破他的幻想。
却还是难忍心中酸涩,一边哄一边强制扭过他的脸,似是气急了一般咬上他的唇,含在齿间带着惩罚意味狠狠厮磨了一番。
扶襄吃痛地低低叫一声,颤巍巍闭着眼倚在他的怀里,乖顺地张开嘴,甚至讨好地伸出舌尖舔他的唇缝。
晏子默瞬间就没脾气了,但再一想到他想的是谁才这幺做的时候,又是一阵郁气直往上涌,愣是抱着他缠绵了好一会才暂压下来。
扶襄早已体力不支,轻喘着歪倒在他怀里,方才还苍白的唇变得水光粉润,好似被刚刚疼爱过。
自他回京染病在榻,今天已是第三日。晏子默担心得茶饭不思,终于见到人却被当成了旁人,怎能不叫他又爱又恨。
这会扶襄又清醒了过来,病恹恹地喝下他端过来的温水后,便脱力一般躺回了床上,强撑着精神问:“你怎幺过来了?朝中发生了什幺事?”
“没有什幺大事,”晏子默给他盖好被子,眼神柔和,“你闭上眼安心休息,别硬撑着。”
闻言,扶襄轻嗯一声,弱弱地闭上了眼,只是眉头微蹙,呼吸也时轻时重,明显情绪极不安稳。
晏子默是心疼的,然而也无能为力,并且这副模样是因为别的男人,他只得压抑着,放轻声音哄他。
等到床上的人彻底睡过去,他在床沿缓坐片刻,便起身离开,然后径直去了御书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