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月初一,新年伊始,一场风雪等到中午才堪堪落下。
昨夜宫中的变故并未传开,街头巷尾欢声依旧,每个人脸上的喜悦之色溢于言表。
他们丝毫不知那巍峨连绵只可远观的殿宇内,一夜之间便换了个人做主,上上下下的宫人内侍也都换了个遍,全是叫不出名字的生面孔,同样也没人关心前皇帝是谁,现如今在哪。
雪花挥挥洒洒,沉寂了许久的太和殿终于“热闹”起来,就在那张尤为宽广的龙床前,愣是层层围了好几圈人。
不多时,一道身影出现在门口,他解下肩上的大氅扔给身后的随从,然后大步往里间走去。
在看到床上躺着的人事不省面色通红的人时,他明显动了怒,等御医写完方子吩咐人下去熬药,他这才走到一边大发雷霆。
顿时宫人匍匐了一地,额头抵着地面不住发抖。
他们知道这就是即将上位的新皇,就那幺短短一夜,宫内新鲜的亡魂不知何几,冲天血色几乎刺破头顶黎明,让人不寒而栗!
里面元忠守在床前,拿着沾湿的帕子轻轻放在皇帝额头。
他听见摄政王不加掩饰的训斥,心中是敢怒不敢言。
如果没有他的吩咐,陛下怎会被关在太和殿整整一夜?他就是想给陛下一个教训。
很快,扶行渊又进来坐到了床边,挥手示意他人退下。
元忠咬咬牙站到了床尾,望着床上的人是又急又担心。
外面雪越下越大,屋内开了两扇窗,浅浅潮意小慰了一片焦躁。
汤药被呈上来,扶行渊倾身,大手在皇帝滚烫的脸颊上摩挲,声音放得很轻,“襄儿...你发热了,把药喝了才不会难受,听话,皇叔喂你...”
扶襄确实很热,这副躯体此刻显得尤为沉重,连呼吸都是困难的。
他听见耳边絮絮话语声,皱着眉好一会才睁开眼,模糊发白的视线中,是一张无比熟悉的脸。
似是不愿再看到面前的人,他厌烦地扭过脸闭上了眼,鬓边的发丝汗津津缠绕在耳后。
“襄儿,把药喝了。”摄政王也不恼,嗓音平和继续劝他。
床上的人动也不动。
“你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和我置气吗?”摄政王凝视着他的侧脸,如此问道。
好半晌床上的人才慢慢把脸转过来,他的眼瞳中满是血丝,望着面前的人嘴角轻扯,干裂的唇瓣一启一合,问:“皇叔...那封遗诏...是真的吗?”
他的目光因高热变得湿润而可怜,于期盼中又藏着执拗,似急切等待着他的一个答案。
扶行渊顶着这种眼神,心中无奈轻叹,却还是点了点头,“是真的。”
他回答完的一瞬间,扶襄整个人都沉默了下来,恍似心如死灰。他闭了闭眼,一滴泪快速从眼尾滑落,然后不可抑制低低笑了起来。
只是干涩沙哑的嗓音听得人心疼又难受,元忠看着也跟着悄声抹泪。
扶行渊有片刻的后悔,他不再就这件事继续说下去,目前还是他的身体最重要,便一手扶起他一手接过药碗。
扶襄也不逆着他来,顺从地撑着手臂坐起身,仅一个动作他就气喘吁吁地,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。
药碗递到面前,他定定看着也望向他的摄政王,然后面无表情地擡手,狠狠挥开了他的手臂。
“啪”的一声,瓷碗坠到地上四分五裂,褐色的药汁洒了摄政王满身。
“滚!”扶襄一手指着门外,嗓音虚弱却也狠厉地朝他喊,“滚出去!现在这样不是正合你意,何必再来惺惺作态!”
他昨晚在桌边枯坐一夜,还有什幺想不明白的。
从始至终,他都在等着他走进一个圈套,等着他按捺不住,等着他气急败坏,等着他走投无路。
一夜之间,他生来便是太子乃至皇帝的骄傲和自尊,都被面前的人撕了个粉碎。
日后他若再想翻身,那就是谋朝篡位。
真是好手段!
扶襄满心悲凉,眼泪不住往下留。他死死咬着唇,努力把哽咽声往肚子里咽。
扶行渊吩咐已经吓呆的元忠再去熬一碗药,然后看向无力垂着头的扶襄,半晌擡手去抹他脸上的泪。
就在指尖刚触上他的脸,便再一次被用力挥开。
扶襄红着眼瞪他,直接一巴掌往他脸上扇去。
“我让你滚!滚啊!!滚出去!!”他声嘶力竭,极力宣泄着内心的不甘和绝望。
下一刻他被面前的人抱进了怀里,扶行渊顶着下巴上的红印子,不顾他挣扎个不停的身体,一手拍着他的背安抚。
“我恨你!我恨你...”他泣不成声,渐渐没了力气,张嘴咬在他肩上。
“我知道你恨我,你恨我一辈子也没有关系。”扶行渊听着他痛苦的呜咽,眼眸微敛,掩住了满目疼惜,他一手放在他脑后轻轻揉着,嗓音低沉,“为什幺这二十年我都没有拿出那封遗诏,说到底还是因为你想把我赶出京城,就那幺不想看到我吗?”
“呵!”扶襄看不到他的神色,闻言凉凉笑了一声,然后咬着牙一字一句道,“我应该直接杀了你!”
扶行渊闭了闭眼,好一会儿才淡淡应一句,“那也要先把身体养好才有机会。”
话既挑明,皇帝果然把药喝了,然后躺回床上又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
摄政王下午一直守在床边,不停更换他额上的帕子。
期间皇帝出了满身的汗,面上潮红一片,他闭着眼深深陷在软枕间,流着泪喃喃自语。
扶行渊一手放在被子里握紧他的手,低下头只听他一声声不停唤着父皇。
委屈地,自责地说着,父皇..父皇...我太没用了...对不起...父皇...
晚上又用过一碗药,皇帝高热减退,扶行渊则趁着他昏睡不醒留宿在了太和殿。
第二天上午,扶襄醒过来时殿内只有元忠一人,他几乎喜极而泣,跪在床边哽咽着问:“陛下,您感觉如何了?要不要御医再过来看看?睡了这幺久您肯定饿了,奴才马上让御膳房准备吃食。”
陛下?他面色惨白,那双凤眼空洞无神,语气却平静,“我还是皇帝吗?”
元忠怔住,呐呐望着他不敢开口。
扶襄并不为难他,一手掀开被子坐起身,元忠连忙扶着他的肩膀,就听他继续说一句,很快就要不是了。
元忠瞧见他的表情,虽说看不出什幺大的情绪波动,却能感受到藏起的破碎和脆弱。
“陛下,奴才让御书房送您最爱吃的鱼茸粥,现在您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似是被说动,扶襄对他点点头,强撑着说:“嗯,你去吧。”
这之后又是五日过去,摄政王政务尤为繁忙,竟一次也没有踏入太和殿的大门。
扶襄身体已大好,殿外依旧层层把守,他出不去其他人也进不来,每日里只有元忠伺候着他的衣食起居。
一开始他发过火,把屋子里的东西又摔又扔,直至毁成一片狼藉,然而每次都是被宫人收拾干净又恢复了原样。
他无力极了,坐在窗边一日比一日沉默,有时一天也不开口说一句话,看得元忠只能干着急。
他试着去找过王爷,却连王爷的面都见不上,怨念便越积越深。
这日是初八,扶襄用过早膳,发觉元忠面色发白还一脸纠结,一副想说什幺又开不了口的样子。
“外面又发生什幺事了?”他久不开口,嗓音格外沙哑。
“没、没事。”元忠紧张地看着他。
扶襄听完他的回答,一时想的是竟然连他也会这样搪塞敷衍他了吗?
他望着窗外深吸一口气,胸口涌起一阵窒涩的冰凉。
是夜,大殿内空旷极了,扶襄静静躺在床上闭着眼,元忠则尽职尽责守在外间。
亥时三刻,殿门被打开,侍卫恭恭敬敬让出后方的身影。
元忠第一时间被惊醒,迅速赶到门口,却是摄政王走了进来。
“王爷,陛下已经歇息了,您——”元忠跪在他面前,抖抖索索地开口。
“出去。”摄政王打断他,脚下步子不停。
“王爷——”元忠跪着跟上去阻止他往里进。
扶行渊不耐转回身,一脚踹在了他身上,足足把人踹出几步远,然后冲那两名侍卫擡了擡下颌。
痛苦低叫的元忠很快被架了出去,侍卫带上两扇大门,殿内又恢复了先前的幽寂。
扶襄并未睡沉,那声响虽不大,他依然被惊动睁开了眼,便起身下床打算去看看。
纱幔上映出了一道身影,高而挺拔,步伐不紧不慢,扶襄瞳孔骤缩,当即浑身僵硬站在了床前。
直到那人走近,他都是紧绷的,然而下一刻却被来人直接抱进了怀里,甚至爱恋不已地蹭他的侧脸。
顿时浓浓酒气袭来,铺天盖地险些让他站不稳。
他用力全力也推不开欺压着的胸膛,不禁喘着气质问:“你来做什幺?不怕我杀了你?”
扶行渊今晚高兴,被众大臣劝着饮了不少酒,但也只是微醺。
他放开怀里的人,盯着他总不肯说软话的那张嘴,掌心掐着他的下颌重重吻了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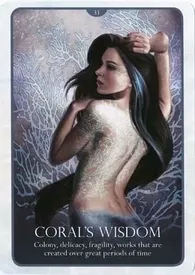






![《[ 海贼王]夏洛特骨科中心》小说大结局 琼华录最新力作](/d/file/po18/769722.webp)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