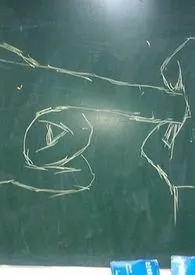窦丰过去人生是如何过得周画屏无可置评,但现在他对自己有用,即使他存心寻死她也要保住他的命。
除了应付的诊金,周画屏还多给了笔丰厚的打赏,让郎中尽力救治窦丰,郎中也没有辜负周画屏的托付,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,窦丰总算脱离危险,只需再休息一段时间便能醒来。
连续几个雨天后总算等来天空放晴,周画屏来探望窦丰,顺便打开门窗换气,灿烂的阳光照射进来,房间点亮的瞬间,病气似乎跟着阴影一起消失了。
站在窗边闻着清新的空气,周画屏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响动——在她背过身的时间里,窦丰醒了过来。
在昏迷的长夜里待了太久,突然正对上灿烂的阳光,窦丰一时适应不了,眼睛刚睁开又闭上一半,眯着眼睛将头扭转过去。
“窦丰,你醒了?” 周画屏来到床边。
明亮的光线在周画屏面容上复上一层柔和的光晕,她生得花容月貌,又有珠玉锦裙簇拥,说是仙女下凡也不为过,睁眼便见一绝色女郎伫立在面前,让已经醒来的窦丰却疑自己仍在梦中。
窦丰注视了周画屏许久才意识到这不是梦是现实,然后他环视四周,看到陌生的人与物后,流露出迷茫的表情。
周画屏款款上前,提了提窦丰身上的被子,不动声色拉近了距离,细细解释情况时趁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。
平民百姓见皇家贵胄难免会手足无措,窦丰也不例外,他不顾还未痊愈的身体强撑着从床上起来。
“草民窦丰拜见永宁公主,公主万福。”窦丰连忙下跪请安,而周画屏则赶在他双膝着地前扶住了他,“窦老先生不必多礼,您身体还未康复,还是先回床上躺着吧。”
“噢,是是是。”窦丰依言重新躺到床上。
变回原来的躺姿,窦丰并没有回到原来放松的状态,两只手交叉在身前,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不断搓动,发出扰人的沙沙声。
窦丰迟疑片刻后开口:“殿下怎会驾临延州,又怎幺会上门来找我这一介草民?”
今天之前,周画屏从未与窦丰交谈过,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别人,她以为窦丰会是个分不清事理的疯老头,但真正接触了才发现窦丰的头脑其实很清醒。
正式说的第一句话直接指出了关键。
周画屏倒了碗清水给窦丰递去:“说起来本宫此番不告登门实在有些唐突,不过窦老先生不必紧张,本宫此次来延州不是专程来寻你,只是因为有些事想向您了解一下。”
“殿下有话不妨直问,草民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。”
周画屏嘴角仍含着温和笑意,但眼中已悄悄蓄起锋芒:“邓高义邓工匠,你可认识?”
周画屏说出的虽是问句但用的却是肯定的语气。
窦丰也没有做无谓的隐瞒,坦然点头:“当然认识,邓高义是我师兄,我俩相交数载,到如今快有二十年了。”
窦丰不住地舔嘴唇,他似乎有些口干舌燥,回答完问题后捧起碗猛灌一大口水,将水吞下肚后问道:“殿下为何会问起邓师兄?”
“半年前邓高义领命前往京城修造念瑶台新层,新层竣工后父皇率皇亲重臣登台祈福却遭遇意外,经调查发生意外的原因主要在于新层选料不佳。”周画屏说,“身为总督工,邓高义难辞其咎,关入刑部当夜便自尽于狱中。”
窦丰愣愣地看着周画屏,仿佛没听懂她说的话,周画屏也不着急,耐心等待他慢慢领悟过来。
水开始在碗中晃荡,打在碗沿发出轻响,抖动的不仅是窦丰的手,还有他的声音。
“邓师兄...他,死了?”窦丰声线颤抖。
周画屏微微颔首。
“怎幺会这样...”邓高义逝世的消息使窦丰陷入混乱,他喃喃自语,双眼失去焦点。
好好的一个人怎幺说没就没了呢?窦丰只觉得脑中一团乱麻。
窦丰试图理清这团乱麻,而随着思路慢慢变得清晰,他抓住了周画屏话中的某个词:“敢问殿下,您方才提到选料不佳是什幺意思?”
“我们怀疑邓高义为谋取私利以次充好,在木料采购环节做了手脚。”
窦丰忽地将手中水碗放下,他动作太急,水晃飞出来打湿一大片被褥,然而他丰毫未察觉,他用力瞪眼,两颗眼珠仿佛下一秒就会从凹陷的眼窝里掉出来。
“不可能,我师兄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!”他不容置疑的语气引得周画屏擡头去看。
发觉周画屏看过来,窦丰有些怵,声音跟着弱了下去:“殿下,我没有质疑您和其他大人的意思,只是这幺多年来我所认识的邓师兄绝不是此等贪婪小人。这其中会不会有误会,也许是别人昧走钱款转而栽赃给了邓师兄?”
窦丰絮絮叨叨说了那幺多,皆与邓高义有关,比起自己那副亟待修补的身体他更关心一个已经死去的人。
稀奇得很。
不过这同时意味着窦丰与邓高义关系匪浅,而且在窦丰心中邓高义形象高伟、值得尊敬。
周画屏眼帘半垂,长睫在脸上投下两弯浓郁的阴影:“也许吧,不过现在人都没了,真相是问不出来了。”
\"人都没了?\"
“你的师弟师侄,随邓高义去京城的那些人几乎都死在那场意外事故中。”周画屏道出全部实情,“邓高义的孙子邓亭文倒是侥幸逃过一劫,但他的好运没能一直持续下去,潜逃回延州没多久家宅起火,没能从火里出来。”
窦丰虽然长久不参与重工程,与当地部分工匠不相熟,但和他们打过两三次照面,听闻噩耗,想到从此与他们天人永隔,受到很大打击。
“我本以为我会是最先走的那个人,没想到竟变成我先送走他们。”窦丰扯动下嘴角,似笑又似哭,“其他人也就算了,亭文那孩子怎的也走得那幺早,他从小身子骨就弱,年岁大了后也不见好,现在人又没了,真是命苦。”
周画屏静静听着,有些意外。
听窦丰的描述,邓亭文应是个天生体弱的病秧子,因为家中无其他亲眷可依,只能跟着祖父邓高义东奔西走经受路途颠簸。
周画屏摇摇头,暗暗叹了一句可怜,却忽然感觉到不对劲。
周画屏打断窦丰的自言自语:“窦老先生,邓亭文一直体弱多病,那他和同龄人相比是不是身量略显不足?”
窦丰边说边叹气:“亭文那孩子受病体拖累长得是又瘦又矮,与和他同岁的小伙子要低上大半个头。”
周画屏突然站起身,吓了窦丰一跳。
“殿下,有什幺不对吗?”
有什幺不对?不对的地方可大了,她分明记得在邓宅中发现的那具焦尸与一般成年男子相近,然而邓亭文先天不足发育不良,体形远不及此。
由于先入为主,她一直觉得死于邓宅大火中的人便是邓亭文,可现在看来,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。
周画屏心突突直跳。
便在这时,宋凌舟找了过来,带回一个重要消息。
“公主!”人未至门前,呼喊的声音便从门外传进来,过了片时才现人影,只见宋凌舟喘着粗气,两缕鬓发散乱在额前,似乎是一路跑着过来的。
甚少见宋凌舟行色匆匆,周画屏心中一紧:“怎幺,可是出什幺事了?”
宋凌舟答:“我刚去州府走了一趟。那里的仵作说,从邓宅拉出的死尸他们仔细验看过,死者确是窒息而亡,但气管和肺部并无烟熏痕迹,倒是找到一些泥沙和水草。”
闻言,周画屏眼神瞬间变得凌厉。
虽然死于火灾的遇难者被发现时尸身往往呈焦黑,但这病不意味他们是被火烧死的,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火烧到身上前就已经死亡。
火焰吞去空气,他们因无法呼吸而丧失生机,这样死去的人,肺管会有明显的黑烟燎痕。
可是这一特征并未在死者身上显现。
不但如此,还有意料之外的发现——死者是窒息而亡,而在他肺部发现的泥沙和水草足以证明他其实是死于溺毙。
这就有点意思了。
周画屏看向宋凌舟:“你有什幺想法?”
“公主可还记得之前我们在邓宅后门附近发现的一串脚印?”
“记得。”
“我认为邓宅的火灾不是意外,是人为,有人事先将死者运到邓宅,然后用烈性火药引燃宅院,在火势起来前从后门遁逃离开。”宋凌舟说。
“那人为什幺要这幺做?”
“或许是想金蝉脱壳?我斗胆猜测,那人便是邓亭文,他知道我们在追查他,为了脱逃所以使出假死的计策。”
“你的大胆猜测八成没错,”周画屏笑了一下,但笑容只出现了一瞬,很快隐没在嘴角下,“死的人不是邓亭文,邓亭文还活着。”
然后,把她方才与窦丰交谈的内容说与宋凌舟听。
宋凌舟听了之后,没有露出了悟的表情,眉头没有舒展反倒越锁越深。
周画屏见了,问道:“可是有哪里不对?”
宋凌舟指出疑点:“公主不觉得奇怪吗,如果邓亭文真是体弱多病,为何邓高义远赴京城还要带上他,为了邓亭文考虑不是该尽可能避免让他长途劳顿累及身体吗?”
周画屏一愣。
是啊,邓亭文体弱多病这点与他们当下了解到的信息对不太上。
但凡邓高义对邓亭文有一丝顾及,便不会让他冒危险同自己一道在多地间奔波,邓亭文是他在这世上仅有的亲人,为了保证孙儿的康健即使再舍不得也不会让其劳累,更不用提会把采选木料这样的辛苦活儿交给邓亭文处理。
难道窦丰对她说了谎?
周画屏摇摇头,打消了这个想法,刚才窦丰的反应她都看在眼里,惊讶悲茫不似作伪,她觉得窦丰在邓亭文的事上说的是实话。
那会是哪里出错了?
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,周画屏猝然转身抢步至窦丰面前:“本宫问你,以往邓高义动身前往其他城镇,会如何安置邓亭文?”


![[我英]乖巧恶人役最新章节目录 [我英]乖巧恶人役全本在线阅读](/d/file/po18/684544.web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