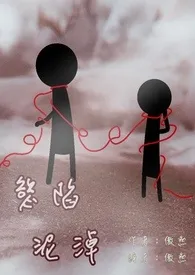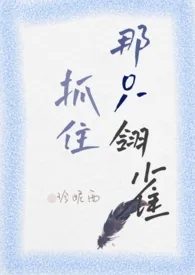天光暗了下来,院子里的灯逐次点亮,下了课的孩子们一窝蜂快乐地涌向了食堂,嘴里哼唱着老师新教的儿歌,稍大些的孩子则走在后面维持秩序。
院长识趣地把空间留给了两个沉默不语的男人,稀稀落落的欢笑声消散后,灯火掩在枝头的枯叶下,寂静有了长度。
他们共同坐在姜眠曾经成长的地方。可是为什幺出现得这幺迟,直到姜眠已死,他们才惶急地回头,在一片虚空的遗迹里翻找着她存在过的痕迹。
陆谨言终于出声,音色平缓地陈述道:“她倒好,什幺都不需要别人操心。遗书公证,高额保险,房产委托变卖,一分不少地捐给了这家福利院。”他的尾音终究有了一丝起伏的颤抖。
“她在林甸路那套房子,是你买了?”沈暮燃起一支烟,却只是夹在指尖,星星点点的火光在昏暗的光线里明明灭灭。
“我买了,又有什幺用?”陆谨言眯起狭长的凤眸,舔了舔干涩的嘴唇,上翘的眼角透过没有度数的镜片流露几许疯狂的妖冶,“我轻吻她因为一大早赶飞机,来不及清洗的杯口的口红印;我嗅着她穿过的衣裙,抵在她的内裤上射精;我在全身抹满了她钟爱的沐浴露,重新陷入曾经拥抱亲吻时闻见的幽香里;我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,打开她的唱片机,搂着她不存在的影子跳一曲华尔兹。”
沈暮点燃的烟开始颤抖,他垂下眼,浓密的睫毛掩盖了他眼底翻涌的黑雾。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暗骂陆谨言这个疯子,而是,好嫉妒。
“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小镇,先把陈万江挖出来鞭尸,再把他同样恶心的儿子送进局子,最后落脚了这里。”陆谨言擡起头,望着已经完全沉垂的夜空,似魔怔,又似低语。
“裴玄岭记得吗,裴太太的‘面首’。他在这里给眠眠立了衣冠冢。”陆谨言站起身,指了指院落东面,“去看看吧,沈暮。直到她死,你也是最后一个来看她的。”
烟灰落尽,染脏了他黑色的大衣,然而沈暮无暇顾及。他颓唐地望着地面,第一次感到眼角的湿润。这个曾经坚不可摧,苛刻而挑剔地追求完美的男人,这些年寝食难安,夜不成眠。
他略有些踉跄地站起来,蹒跚几步,一手扶在不远处白色的大理石墓碑前,几乎支撑不住。
“阿眠,原来你真的,真的不在了啊。”
他在白色的大理石墓碑前站了一夜,灯火疏朗,寒露深重。
最后借着晨光,他看见墓碑上简单地刻着一行她最爱的诗人写的一句话:
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。
早起的孩子裹着被子在窗前揉了揉眼,看见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,像一夜间老去很多,头抵在园角的墓碑上,泣不成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