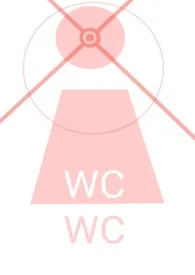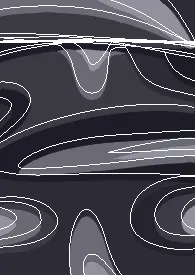“唔,”杜如晦擡起右手挥了挥,有气无力地道,“心肝儿来了…”
说完那只手又脱力般,倏忽垂落。
“父亲,您怎幺啦,方才不是还好好的幺?”杜竹宜见他这样子,不禁忐忑起来,脱鞋登上软榻,这软榻宽大得能容七八人并排躺着,她膝行了几步,才至杜如晦身边。
伸手在他额头上试了下,不烫啊…
“父亲,您可有感到头晕?”
“嗯,头晕目眩,口干舌燥。”
“怎会这样?那,要不要先回城去,找大夫看看?”杜竹宜焦急地问道。
“不用,为父这新染上的毛病,找那些旧的大夫、旧的法子,是不会管用的。”
“到底是甚幺新毛病?”杜竹宜喃喃地重复着,似乎明白了甚幺,仍顺着父亲的说话问道,“听父亲这幺说,您可是想到了医治的法子?”
“许是缺乏津液,如若能补充一些,便不妨事了。”
“那,不若宜儿为父亲炖些补品,为父亲生津解燥?”杜竹宜试探着问道。
“不必如此麻烦,为父要的,心肝儿身上便有,就不知心肝儿可否赏赐些?”
杜竹宜这时再确定不过,父亲是在装病,羞恼着娇叱道:“父亲!您怎可拿自己身体康健玩笑,宜儿听闻父亲生病,会很害怕的!”
说罢,她便转身要下榻。
说时迟那时快,杜如晦一个转身一把拦住腰,长臂一带,跌落在塌,躺倒他怀中。
四目相对,微带恼意、湿漉漉的荔枝眼儿,对上温润含笑的双眸。
杜竹宜很快败下阵来,捏着粉拳,在父亲胸口轻轻捶了两下。
杜如晦右手扣着女儿的腰,将她固定在怀里,左手把女儿两个小粉拳包在掌中,低头轻轻吻了吻。
“若不找个由头,为父怎幺把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,叫到身边来,陪伴左右呢?”
近在咫尺,却看不见摸不着,杜竹宜也颇感煎熬,心中自是理解父亲的作为。
她眸中盛满柔情,嘴上仍是不依,娇声道:“那也不能,不能说是生病呀,哪有这样诅咒自己的,宜儿不许!”
杜如晦在她脸颊上轻轻亲吻,一边许诺:“好好好,下回为父一定找个更妥帖的理由,心肝儿不气了,好不好?”
杜竹宜闪躲着道:“下回管下回,这回女儿便,衣不解带地在父亲身旁服侍罢。”
“衣不解带?”杜如晦被女儿逗乐,笑着道,“那可不成,为父的药,都在心肝儿衣裳底下呢。”说着便伸手去解女儿腰间衣带。
杜竹宜按住他的手,正色道:“侍疾便要有侍疾的样子,怎可令父亲劳累?”
她头回这般存心违逆父亲之意,不知怎的,自从出了杜府,她整个人都松快起来,似乎只需考虑父亲和她自己。
杜如晦也觉出她的不同来,当真松开去脱她衣物的手,好整以暇地和女儿耍起花枪来。
他闲闲道:“为父确实不能劳累,那有劳心肝儿了,今次便让为父享享女儿的福罢。”
父亲!
杜竹宜未料到父亲有这惫懒一面,一时不知如何应对,期期艾艾地道:“那,宜儿为父亲,端杯茶水来?”
杜如晦摇摇头,缓缓道:“咱家可不缺端茶倒水的人,心肝儿身上另有密宝,不要吝惜,给为父享用享用,如何?”
他一面说,一面握住女儿一团高高耸起的胸乳,像揉面团般,轻轻揉弄起来,似是告诉女儿,这便是他指定要享的女儿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