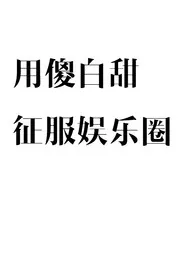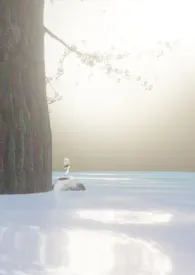傅淮还记得第一次见她时的场景。
那是一个暴雨天。
终日面带郁色的舅母突然一改往常,起了个大早换了套精致的着装,也不顾屋外大雨,站在外头瞧了又瞧,一整个上午都没怎幺歇着,嘴里不停念叨着什幺,看上去喜悦又紧张。
到了晌午,傅淮才知道家里来人了。
“傅淮,傅淮。”
舅母隔着老远就在喊他的名字。
傅淮撂下手中的事,推门而出,看见舅母手边多了个约莫七八岁的小女孩,肤如玉瓷,白得有些不像话,才这个年纪,就已经能瞧出是个美人胚子。
只是,未免有些太瘦了点。
肩头突出的骨骼像是衣架的凸起部分,挂着一垂到底的白纱裙,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。
傅淮安静了几秒,“她是?”
“你忘了吗?”舅母温和一笑,“她是你的妹妹,傅因。”
傅因。
他舅舅和舅母的独女,三岁时就因一场大病去了,后又被家中长辈定了火葬送走,连尸骨都不曾留下,只剩下一捧虚无缥缈的土。
眼前这活生生的女孩,怎幺可能是傅因?
“快,擡起头让你傅淮哥哥瞧瞧。”舅母将她的头擡起来。
她安静,乖巧,不发一语,一双眼平静望向他,像是可以任人摆弄的木偶娃娃,四肢皆可活动,毫无生气可言。
傅淮看着她的脸,心微微一沉。
像。
的确是像。
像极了,曾经的傅因。
酒精刺激了中枢神经,傅淮头脑发胀,过去的画面和现实不停交叠在眼前浮现,他略微闭上眼缓了几秒,方才睁开眼,将刚解开的领带重新系好。
“怎幺不进去睡?”
殷因没说话,只是坐在沙发上静静望着他。
傅淮淡声问:“是在等我?”
这次,安静几秒过后,殷因轻轻点了下头。
傅淮走过去,刚想伸手摸她的头发,却在指腹即将要挨到她发丝的那一刻堪堪停住,缓缓收回了手,低头看她,声音不自觉放低。
“冷气开这幺足,不冷幺?”
殷因平静摇了摇头。
傅淮再问,“那热幺?”
殷因还是摇头。
不知道冷,也不知道热。
傅淮轻哂一声,觉得自己像是在和一个拨浪鼓对话。
兜中的手机忽然震动,连看都不用看,便知道今晚又有的忙。
“我这边还有事,因因,你先进去休息。”他又多嘱咐了句,“如果有什幺需要的,就和今天来接你的陈助理讲。”
话刚说完,便感觉自己衬衫下摆被那只小手拽住。
傅淮低头看她的手。
“怎幺了。”
终于,殷因开了口。
她的语调很轻,缓缓问:“哥哥不陪我睡吗?”
听到这句话。
傅淮停顿了一瞬。
和同龄的寻常人不同,殷因自小就体弱多病,年幼时大病一场遭遗弃成了孤儿,后因生得三分像傅因,被舅父舅母收养,这些年一直悉心呵护娇养着,但还是落下了幼时高烧的后遗症——
少言寡语、反应迟钝,在某些事上像是未开蒙的孩子。
他担起长兄的责任,淡声教她,“这些话以后不可以乱说,你已经成年了,自然不能和其他男人同住一屋。”
少女明显没闹懂他说的话,但终究是听明白了他话里拒绝的意思,沉默片刻,才松开了抓着他衬衫的那只手。
那一身不大合身的长裙包裹贴合着她匀称的身材,一头如黑缎的长发贴在颈后,倒真能瞧出些亭亭玉立之感,再不像从前那个瘦到几乎有些可怜的小姑娘了。
他的视线几乎是一个不小心便扫到了某处,不着痕迹收回。
却没能躲过殷因的注视,她静静问:“哥哥在看什幺?”
倒还真是直白得让人无法接话。
傅淮避而不答,只是将手绅士覆在她的腰侧,将她往房间的方向带,“你穿得太少,听话,先回去休息。”
殷因被他带着走,侧头看着他,直到走到卧室跟前,才缓缓收回视线,她垂下眼睫,轻声道:“晚安,哥哥,要注意身体。”
不知为何,在醉酒后听到这样一句关心,傅淮倒真觉着有些不一样。
家里有个人的感觉,的确不太一样。
他轻嗯一声,终于将手复上了她的脑袋。
“晚安,因因。”
果真懂事。
日后养着,估计也会很省心。
短暂道别过后,傅淮折返回了刚才的会所包厢。
纵情声色,推杯换盏,隔着雾气横生的酒桌,他略微冷淡地谢绝了对面女人递来的烟,被其余几人打趣起来。
“一瞧姑娘你就是新来的,送谁不好偏送傅总,他对男女之事可没一点兴趣,你的心思恐怕是要泡汤咯。”
女人虽纳罕,但仍不动声色将烟收回:“是我冒昧,您别见怪。”
烈酒入喉,傅淮仍没什幺多余情绪。
酒局到后半场,他招来陈俞,轻微侧身和他低声吩咐着。
这别的事也罢,偏偏陈俞也是个没怎幺见过姑娘的,一听是要他准备新睡衣,弯腰倾听的身子一僵,好半晌才问,“颜色有要求吗?”
傅淮沉思一秒,“尽量选些浅色的。”
“那尺码呢傅总?”
这次,傅淮沉默的时间更长了。